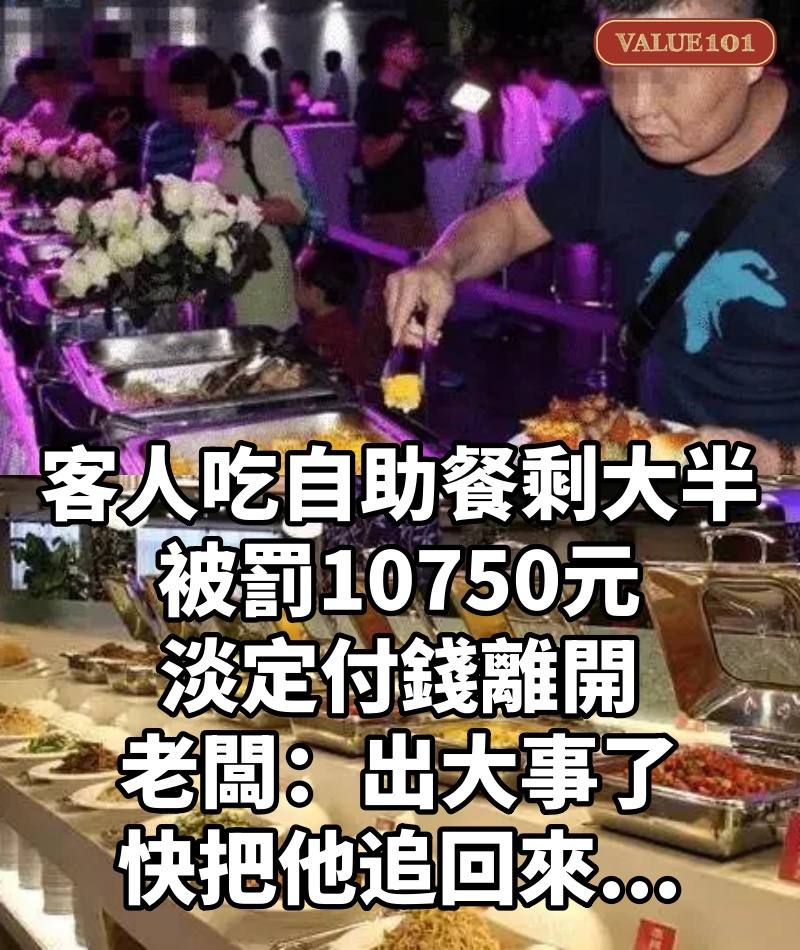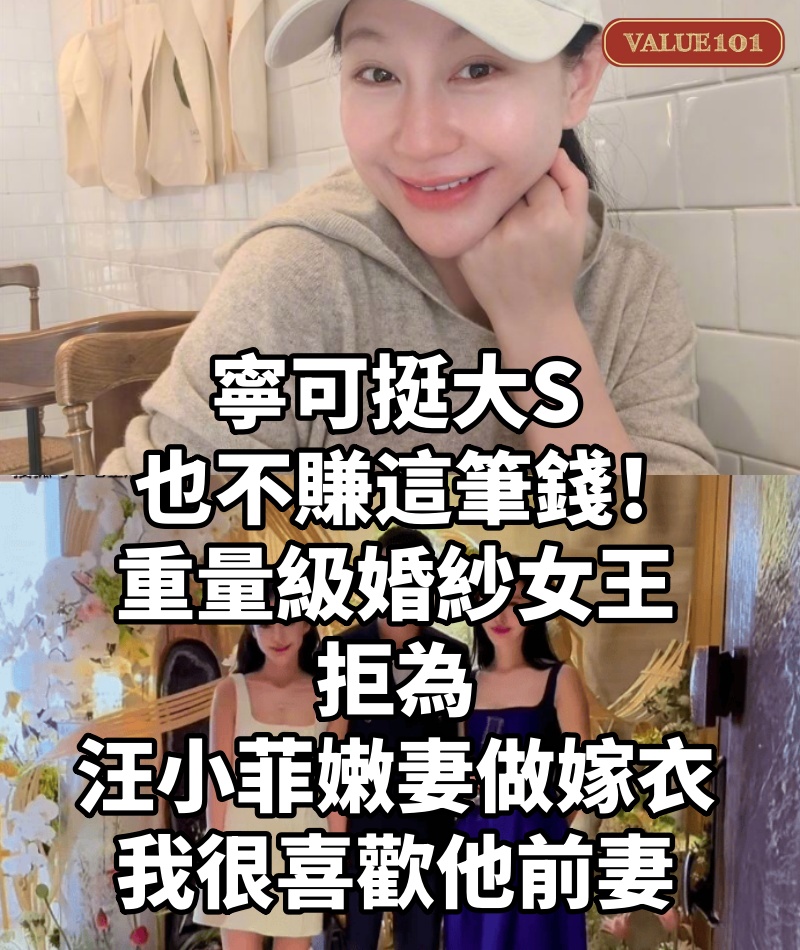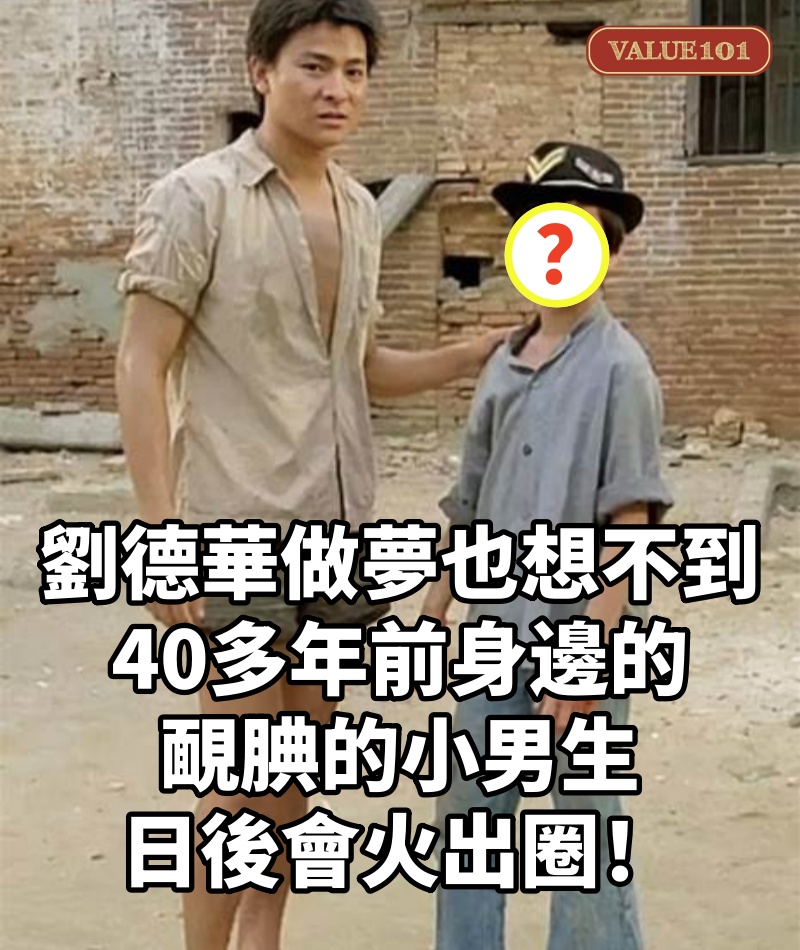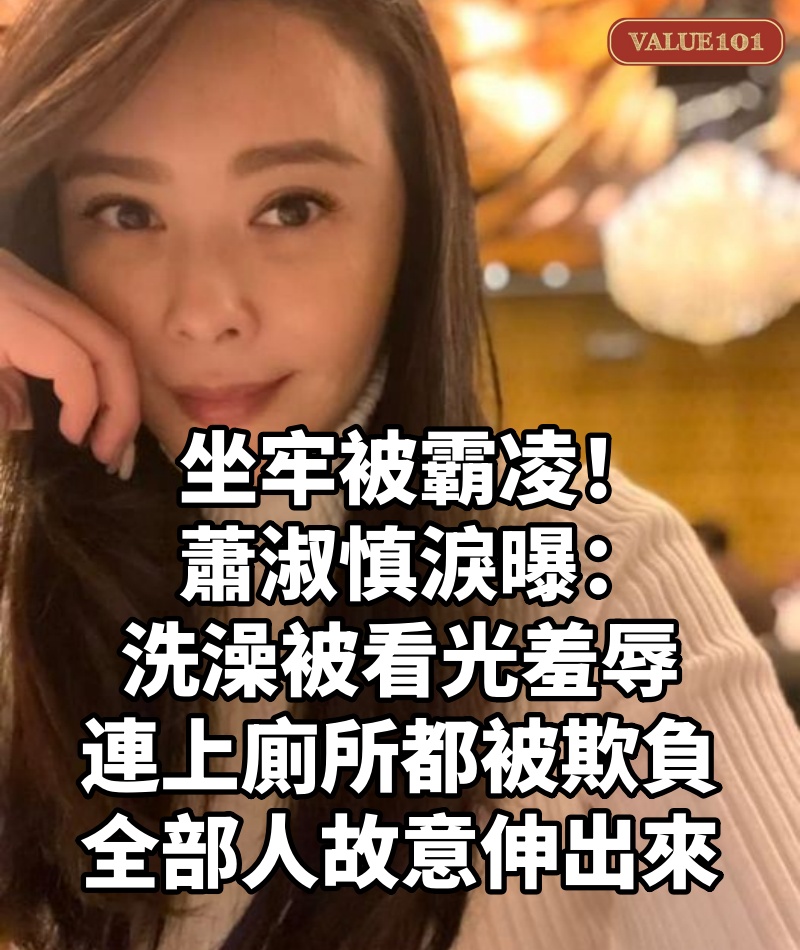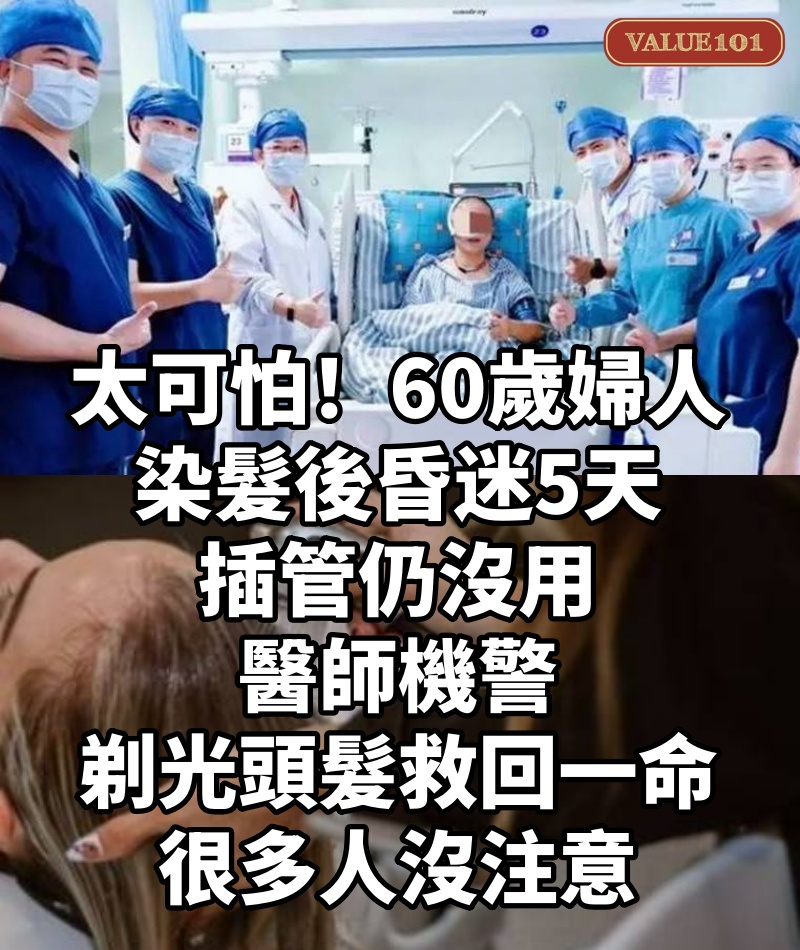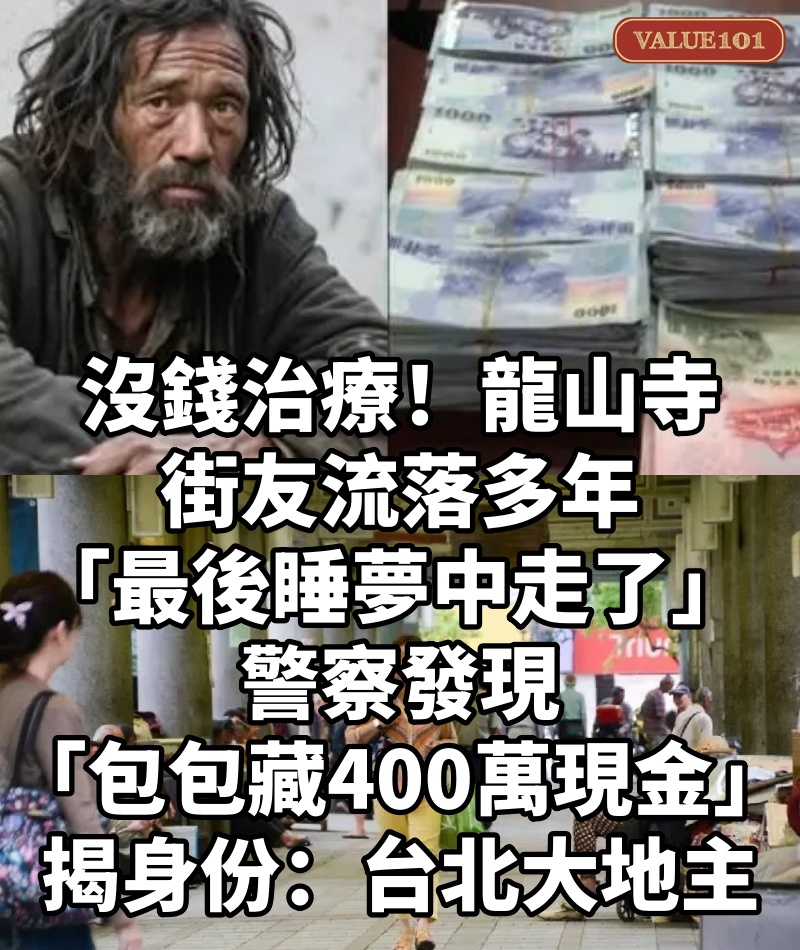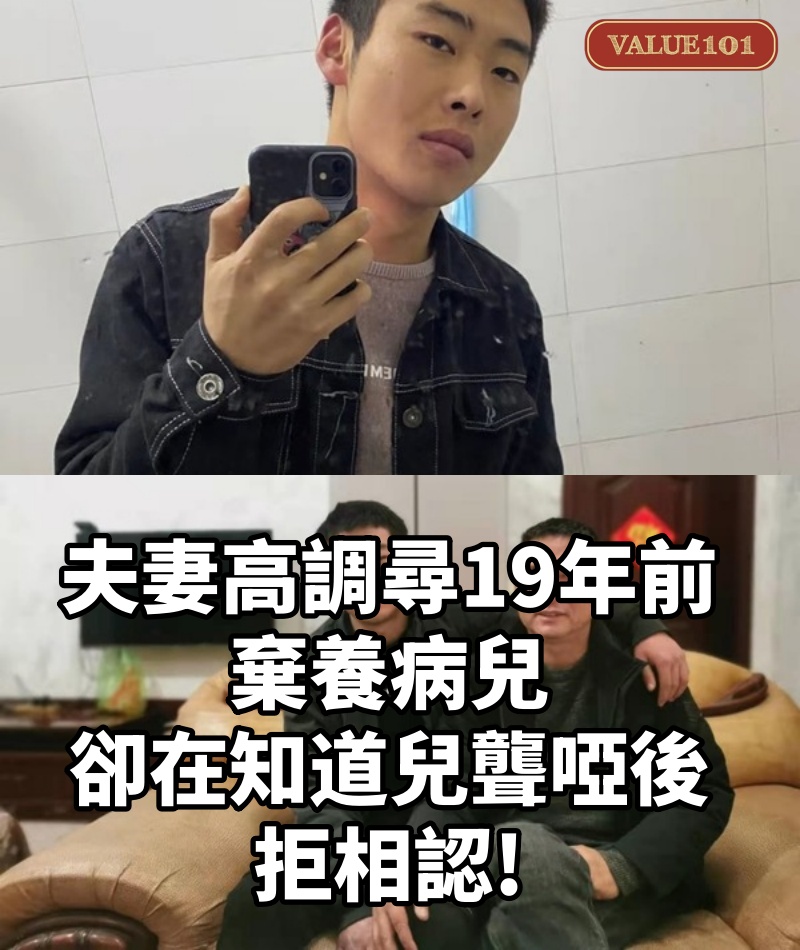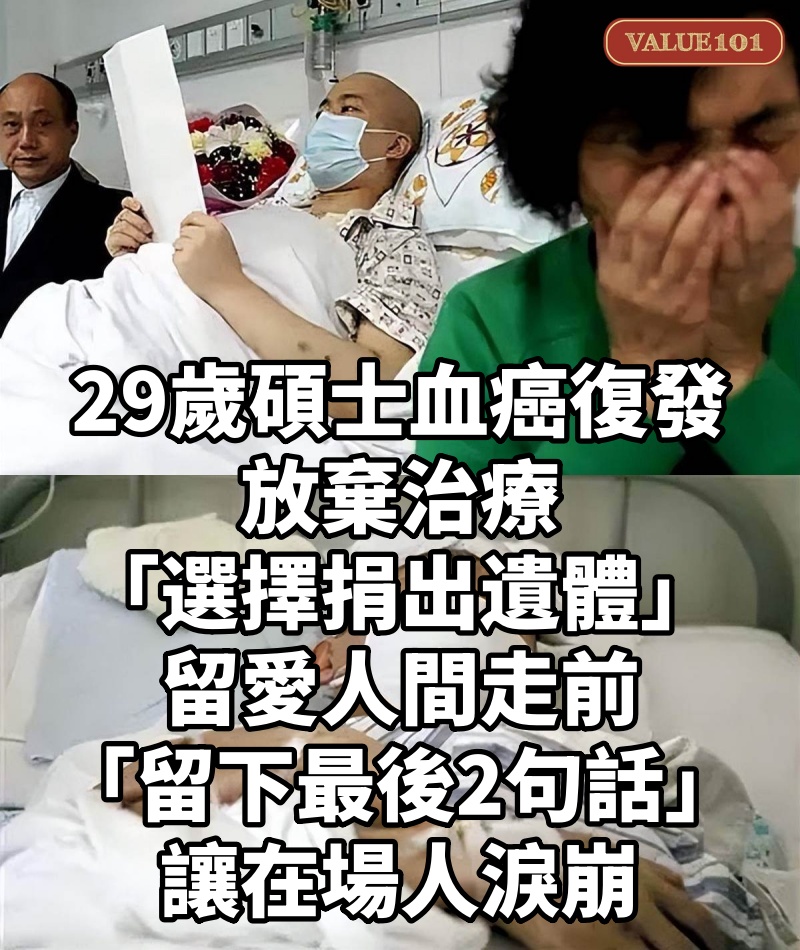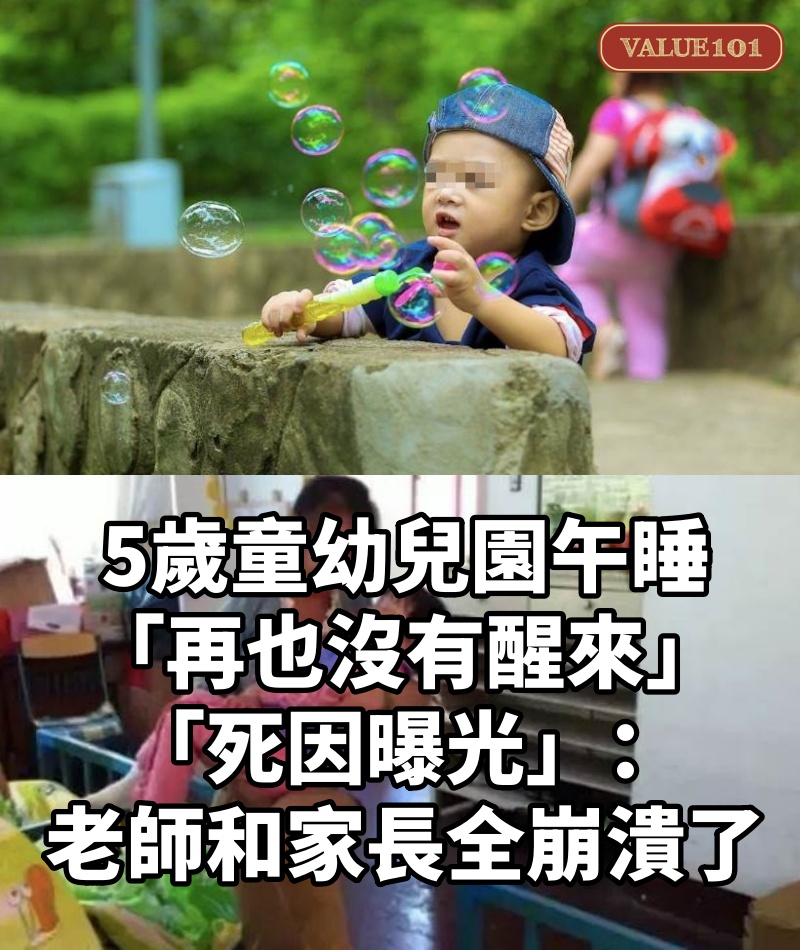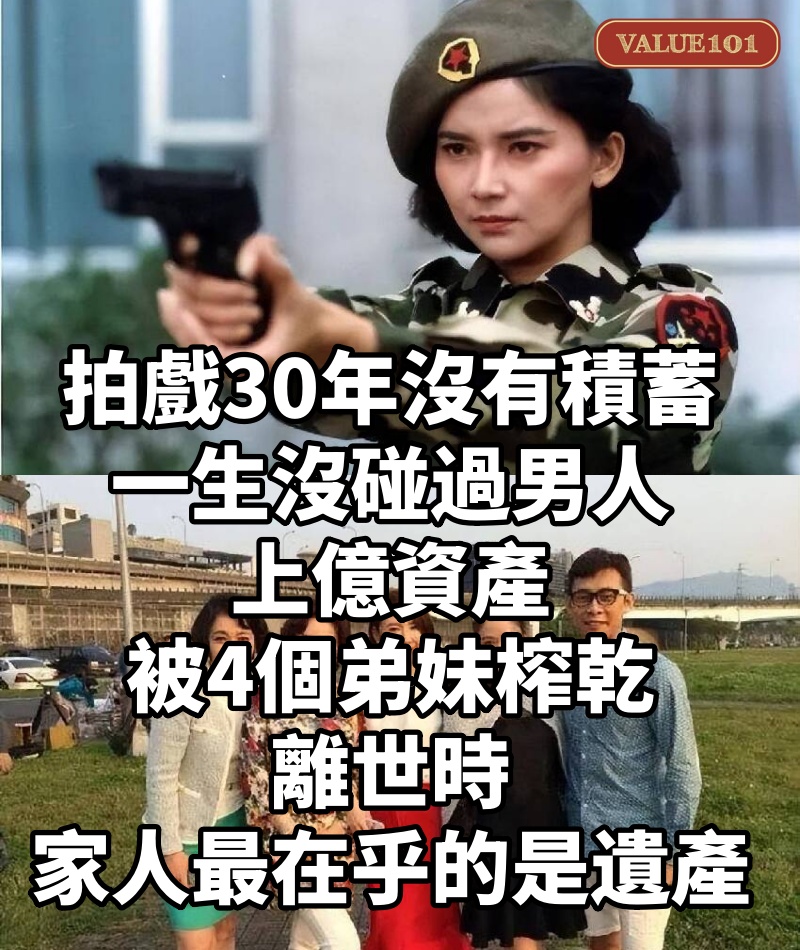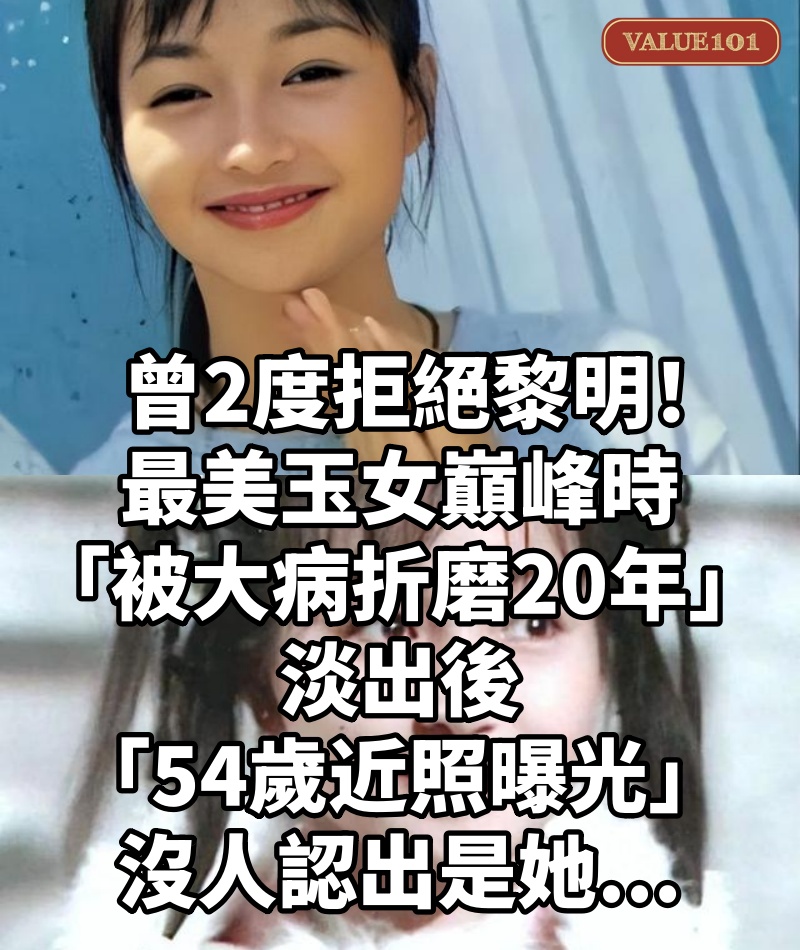父母總做這件事,孩子會變得不幸

朋友小遊今年28歲了,依然時不時收到媽媽寄來的“愛心包裹”。
上次是一雙拖鞋,亮粉色,大兩碼;
上面印著一隻小貓,是她自己一定不會買的款式。
即使說了很多次不要,媽媽還是會不定期寄來一些“有用”的東西。
還有一次和媽媽電話,又問了和往常一樣的問題:
你吃的好不好,有沒有出去鍛煉?
一個人住會不會害怕,工作上有沒有不愉快?
這些擔憂、害怕的話,三番五次地說,小遊耳朵都快起了繭子。
便開了句玩笑,說:
你們老說自己六七歲就會做飯,為什麼我都三十了,
還是擔心我沒有自理能力,不會置辦生活用品?
媽媽聽完後怒了,語氣裡透著失望:
你大了,是不是不需要我了,要擺脫我了。
如果覺得我管的多,以後什麼錢都不要問我們拿。
在和父母的交往中,我們總是遇到類似的情況:
被強行關心、過度擔憂。
無論多少次和他們溝通,希望他們能放平心態,先過好自己的生活,彷彿永遠聽不見。
旁人看來,孩子才是白眼狼,爸媽是受傷的那一方。
總之,雙方心裡都藏著巨大的委屈。
01 “幸福”背後,是被壓抑的需求
父母對小遊的愛,從小就是濃度極高的。
高中那會兒,為了能跟上營養,小游從住宿轉為走讀,和父母住到一起。
住一起後,媽媽每天五點起來做飯。
蛋餅、包子、炒飯換著花樣。
每天都要看著小遊吃完,目送她去上學後,再回去補覺。
但事實上,媽媽非常不喜歡做飯,也不太會做;
加上起得太早,整個人常常頂著一股怨氣。
如果小遊起晚了,吃的少了,母親的怨氣就有了出口。
久而久之,小遊感到難以忍受,向母親提議:
既然我們都不開心,那不如給我3塊錢,在上學路上買個餅吃就可以了。
母親聽完感到憤怒又委屈,說:
“我早起做飯為了誰?外面的飯比家里香嗎?”
“寒冬臘月那麼冷,每天起床給你變著花樣做飯,嫌這嫌那你像話嗎。”
小遊的想法很簡單,希望媽媽可以多休息,早上也少一些爭吵;
可是媽媽一心想為了孩子好,傾向於把它解讀為“孩子不領情”、“孩子叛逆、貪吃”。
這複雜的情緒背後,其實是對“孩子照顧不好自己”的擔憂。
父母對孩子缺少信任,才會像攝像頭一樣,時時追踪、事事照顧。
溫尼科特提出過一個概念,叫做“母嬰間隙”。
表示母親與嬰兒、孩子與家庭之間,需要留下小小的縫隙,才能更好的相處。
如果父母與孩子靠得太近,就像同一部電梯里站了太多人;
孩子的身體無法轉動,無論做什麼,都感覺有人在盯著,感到壓抑、受控。
這個“間隙”被創造出來的條件,是適當的信任;
需要父母,把孩子當做有主體意識的人去看待和尊重。
而實際情況是,父母總想和孩子靠近,發展出一種“假性親密”:
自我犧牲,把我認為好的給你,你必須欣然接受。
《假性親密》一書中,提到過一種防禦性的相處模式。
即在關係中,一方扮演“表演者”,另一方扮演“觀眾”。
表演者忽略自己的感受,自顧自扮演著“好父母”的角色;
作為觀眾的孩子,被動接受對方的付出,提出異議很難被聽到。
在旁觀者看來,父母很愛孩子,關係十分親密;
但只有身處其中,才能感覺到,“雙方感受都沒有被照顧到”的絕望。
02 “看不見人”的關心,背後藏著什麼?
大學剛畢業那年,父母來到小遊的城市看望小遊。
走進小遊的臥室,母親說了一句:“地板有些臟”。
小遊心想,之後用吸塵器吸一吸,再用拖把拖一遍就好了。
可媽媽就是不同意,親自跪在地上,拿起抹布,一點一點擦除地上的印記。
室友路過表示:“你媽媽真愛你啊,親自過來打掃。”
媽媽接話:“是啊,我家小游從小就不會收拾,你們多多擔待了。”
站在一旁的小游絲毫開心不起來,反而感到異常的彆扭——
明明自己獨自生活,也能過得不錯;
為什麼媽媽眼裡,自己總是做得不好?
現在她快30歲了,偶爾給父母分享生活照片,他們還是會忍不住說:
衣服穿少了,下次不要露腿。
旁邊的是誰呀,都是女生一同去的嗎?
晚上回去不要太晚了,最晚9點。